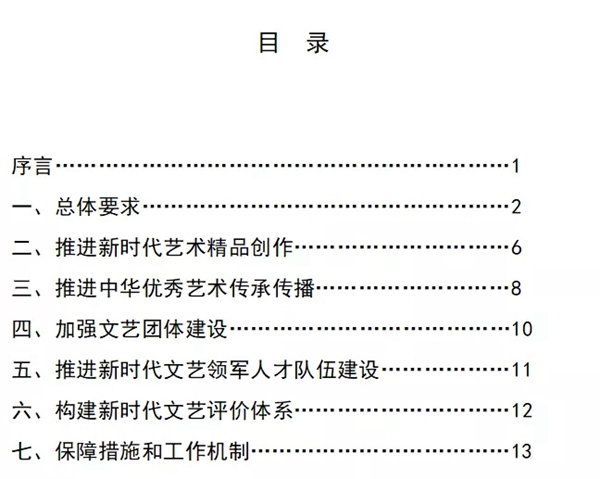秋兰为佩 煌煌满辉——送别陈佩秋先生
时间:2020-07-03 10:25:38 来源:上海中国画院 作者:
秋兰为佩 煌煌满辉——送别陈佩秋先生

送来花篮的中央及上海市的领导有:李强、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陈至立、杨振武、徐麟、慎海雄、龚正、董云虎、杨雄、殷一璀、姜福堂、陈铁迪、王力平、蒋以任、龚学平、刘云耕、冯国勤、金炳华、王仲伟、廖国勋、郑钢淼、周慧琳、诸葛宇杰、陈群、宗明、方惠萍、朱争平、朱晓明、杨定华、赵雯、陈靖、虞丽娟、胡劲军、高韵斐、王珏、于秀芬、尤存、奚美娟、樊嘉、陈东、施大畏等。
出席告别仪式的领导有:龚学平、刘云耕、金炳华、朱争平、胡劲军、于秀芬、樊嘉、陈东等。
出席告别仪式的领导亲切慰问了陈佩秋先生的家属。告别仪式由曹可凡主持,画院院长陈翔介绍陈佩秋先生的生平,家属代表谢定伟致答谢辞。
今天到现场送别陈佩秋先生的还有她的至亲好友、各级领导、画院同仁、学生弟子及各界人士近800人。

慰问陈佩秋先生家属

长无绝兮终古——怀念陈佩秋老师
文| 徐建融
2020年6月26日凌晨,惊悉陈佩秋老师突然去世的噩耗,不胜哀悼!历历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到眼前。
回想自己有幸认识陈老师并得到她的指导,至今已有48年的时光了。1973年,我的启蒙老师姚有信先生调入上海画院,我便常去画院请教。姚老师则领着我去拜访其他的名家,使我结缘了一大批早在中学时代便已仰慕的前辈,陈老师正是其中的一位。据她后来告知,当时她所在的画室,是由车库改造而成的。入门是一小间,应野平、朱梅邨两位先生各摆一张画桌;右转进入主室较大,唐云、孙祖白两位先生对面并排两张大画桌;向后则陈老师单独一张画桌,入内又是一小间,胡若思、徐元清两位先生对面并排两张画桌。在我的记忆中,陈老师是对年轻人最热情、最健谈的前辈之一,她的许多见解,都是我所第一次听到,印象深刻却一时难以理解;再加上我当时的艺术追求,兴趣广泛而不拘一格,所以直到80年代之后,才认定了陈老师的艺术观作为自己追随的方向。
陈老师对我所讲过的艺术问题,我概括为三条:
第一条,艺术的创新不仅要新,更必须“美”而且“难”。这是当时我向诸前辈请教历史上的一些名家“谁比谁画得更好”时,有些前辈认为只要是个性的创新,就没有可比性,都是好的;等持此说的前辈离开画室后,陈老师便对我说:“虽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艺术还是可以比较的。如果只讲个性的创新,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比如写一横,大家都是左低右高,你写成左高右低,就是与众不同的创新。但这样的创新,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当你的创新,不仅是个性的,而且是美的,更是别人难以做到的,才真正具有艺术的价值。”后来她还告诉我,年轻时在美院学习,黄宾虹先生告诫她赵幹的《江行初雪图》是匠气的下品,翁松禅的翰墨游戏才是高品,她正是以“美”和“难”为标准,认定了唐宋的画品。再后来,读到莱辛在《拉奥孔》中定义“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钱锺书在《七缀集》中认为不同的艺术风格是“平行不平等”的,对陈老师的“美”“难”观就真正敛衽无间、五体投地了。

第二条,是唐宋传统。讲到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便牵涉到如何认识传统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我们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便是以唐宋传统为封建性、贵族性的糟粕,而明清传统则为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再往前,便是以唐宋传统为工匠的俗气,明清传统为文人的雅事。而“工笔画”一般被作为唐宋传统的主流,“写意画”则被作为明清传统的大潮。这个偏见,从董其昌之后便广泛地传播开去,直到陈老师的年代,“泼墨写意大丈夫,闺中女儿描工笔”,“工笔画是包小脚,写意画才是天足”,诸如此类的论调,屡见不鲜。陈老师却以“美”和“难”的标准,对唐宋传统深信不疑,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唯写意是传统的形势下,她的这些成就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认可。因此,一方面为了反驳“小脚”不能变“天足”的偏见,另一方面也为了在解决形象问题之后进一步提升笔墨境界,她从70年代开始用功于写意传统,主要学习徐渭、八大的传统,包括画撇出的兰竹。有一次,有一位同辈看到她在画兰竹,便对她说:“兰竹,郑板桥画得最好了,你为什么不学他的呢?”陈老师笑笑而已。等那人走了,便对我说:“郑板桥、扬州八怪,他们的画格调不高的。大写意,徐渭、八大、石涛才是高格调。”
总之,在陈老师看来,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只有一元;而任何一元中,都可以做到优秀,也可能萎靡不振。而无论学哪一路传统,不能光学它的“然”即图式样本,更要学它的“所以然”,即这个图式样本之所从来。在唐宋画,这个“所以然”便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写生;在明清画,这个所以然便是“三绝四全”的“画外功夫”。陈老师在学习唐宋传统方面所下的功夫,在我看来自古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做到过。她临了多少宋画,一幅幅都“下真迹一等”;她更作了多少写生,每一幅都足以“夺造化而移精神”;她学习写意画,结果不是用写意的笔墨去作“不求形似”,而是用写意的笔墨来作更精练的“形神兼备”的写生!
今天,年轻一代中学习唐宋传统的人越来越多,成了一件时尚之事;但又有几个能像陈老师那样在“逆流”形势下学习唐宋传统的精神和意志的呢?进而,如果我们学习唐宋传统的出发点是为了对抗、贬低甚至否定明清传统,我想,这更不是陈老师倾其毕生心力倡导唐宋传统的本意。
第三条,是“中西交融”。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凡是传统的拥趸,都偏执地认为“中西绘画必须拉开距离”,而决不能搞“中西融合”。因为,中国画和西洋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绘画,只能各行其道,不犯河井;如果“中西融合”就必然沦于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最终葬送传统的前途。陈老师则完全不为这种所谓的“传统自信”所囿。
70年代的陈老师,不仅致力于写意画的传统,并表现出对西方绘画、尤其是印象派的关注。当时画院中有不少进口的印象派画册,再加上林风眠先生的影响,陈老师还有程十发、姚有信等几位先生均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同程度的热情和兴趣。有一次,她在看莫奈、雷诺阿的画册,便对我讲到,中国画的毛笔尖、齐、圆、健,比油画的扁笔表现力要强;但西洋画的色彩实在太美了,流光溢彩,像梦幻一样,是中国画所够不上的。后来,有一位香港朋友吧?送了她一些外国颜料,真是丰富多彩,光绿色就有十几种。她一试,兴奋得不得了,对我说:原来中国画的“水墨为上”、彩色为俗,是中国的颜料品种太少了,画不出灿烂高华的效果;而西洋画的色彩美,与他们的颜料品种丰富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送了我一大盒外国颜料。我至今还保留着七八支,都已经干硬了;但浸泡后化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透亮而无渣。80年代,她有机会走出国门,进一步发现西洋画的色彩美,除了颜料品种的丰富,更与其城市如花园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益信“生活为艺术的源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除了印象派,70年代时她受伦勃朗的影响也很深。她曾对我谈到花鸟画的构图,从宋人一直到华新罗,凡是禽鸟一定处于枝叶稀疏的空白处,所以显得“主体突出”;独有任伯年,常常把禽鸟隐藏在枝叶茂密处,这就显得匠心独运、高人一筹;但有一个不足,就是观者一下子看不到禽鸟在哪里,需要慢慢“寻找”。如何解决茂密处的禽鸟也能显得“主体突出”这个难题呢?便是伦勃朗将主体人物置于群像之中,却又把“高光”打在他身上的处理办法。我们看陈老师7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花鸟画创作,无不繁枝密叶、景深丰邃,而透光之处,便是禽鸟的飞息之地,使禽鸟虽深藏不露,却又一目了然。

陈老师的艺术,之所以能成为传统底蕴与创新精神深厚鲜明的典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完美融合的典范,笔墨美、色彩美、形象美、意境美四美兼备的典范,以我的认识,是与她对上述三条一生如一日地自觉研求分不开的。有人将她的成就归诸于她的天赋,她并不完全认同。她认为,一定要讲“天赋”,其实只是“爱好”;但光有爱好、天赋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功。光有用功还是不够的,必须是在结合自己的正确方向上的用功。而上述三条,正是适合于她的正确方向,也是适合于大多数人的正确方向。“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正宗大道,也有旁门奇径,不能用这一条去否定那一条,根本的是要认准适合于自己的一条。
陈老师的去世,媒体上多有“最后一位大师走了”、“传统中国画从此画上了句号”的扼腕三叹。这种说法,当然是对陈老师艺术成就的褒奖,但我想陈老师本人是不会同意这么说的。当年,李可染先生去世了,媒体上认为“中国画的最后一位大师走了”;陆俨少先生去世了,媒体上认为“中国画的最后一位大师走了”;黄胄先生去世了,媒体上又认为“中国画的最后一位大师走了”……对此,陈老师始终是不同意这么说的。她认为,中国画也好,中国文化也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它是生生不息的,如“子子孙孙,永无穷尽”,不可能有“最后一位”,也不可能有“句号”。
今天,大家缅怀陈老师,都推崇她的性格要强、好胜、不让人。这当然是一方面,但只是表面的。她性格的另一方面也是本质的方面,就是谦虚、谦让,尤其在传统面前,更是满怀谦卑的敬意。她以“健碧”为字,便寓意了她甘做绿叶以衬红花的不争;她以“高花”名阁,同样寓意了她让人头地的虚怀若谷;在传统面前,她更自认是一位学到老、学不了的“小学生”。耶稣教认为,家庭中的父亲和儿子,在“上帝”面前都是“儿子”,是“兄弟”的关系。陈老师则常常讲到,现实中的老师和学生,在“传统”面前都是“学生”,是“同学”的关系。尤其对于年轻一代,她认为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使得学习的条件越来越好,后人完全有可能超越前人。所以,传统不会画上“最后”的“句号”,是她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她说,早在她的学生时代,中国画便不被某些人看好,认为传统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了,再也不会有前途了;但事实上不还出现了齐白石、黄宾虹、吴湖帆、张大千、潘天寿、李可染、陆俨少等一大批杰出的画家?至于近几年间“最后”之后又有“最后”、“句号”之后又有“句号”,更足以证明“最后”和“句号”都是不存在的。

陈老师擅画花鸟、山水,兼作人物。在她所拿手的多种题材中,如果要挑选一个具有“形象代言”的标志性符号,那便是兰花。工整的、粗放的,水墨的、彩色的,天工清新出无穷。兰花为国香,在诗中的绝唱是屈原的“美人香草”之思;而陈老师的艺术人生似乎正是从屈原而来,又追随屈原而去。她的“佩秋”之名,出典于《离骚》的“纫秋兰以为佩”;她爱用的“无绝”闲章,出典于《九歌》的“长无绝兮终古”。屈原于端午日离开人世;2298年之后,紧随着端午的次日,陈老师又离开了我们……太史公曰:“与日月争光可也。”敬挽联为祭念:
纫秋兰以为佩,长无绝兮终古;
正梅雨暗江南,礼国香其永馨。
徐建融
2020年6月28日于海上后翠微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