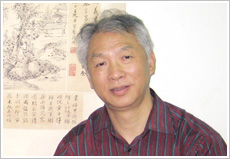男女狂欢 在这场祭祀后
时间:2022-02-14 15:56:39 来源: 作者:
男女狂欢 在这场祭祀后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交大科史哲 ,作者江晓原
本文原载《中国文化》2021年秋季号,作者江晓原先生。

春秋时宋、卫、燕、齐、楚等国皆于春分日在固定地点举行「 高禖之祀 」,。高禖之祀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是「万舞」,这是一种起源与军事有关、因强调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诱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传统可能形成于西周,秦汉以后仍保持了很长时期。在生殖崇拜和阴阳天人感应思想作用下,这个传统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后继之以「仲春之会」,即一种可以放松性规范的「男女狂欢之会」。活跃性生活有利于人口繁衍,同时也有助于青壮年男女「 释放情欲」。仲春之会也可从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对其他文明中类似聚会的描述中得到印证。仲春之会还带有 巫术色彩,被认为有助于年成丰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后世被变形为祈雨等活动,这些活动中仍然强调男女之间活跃的性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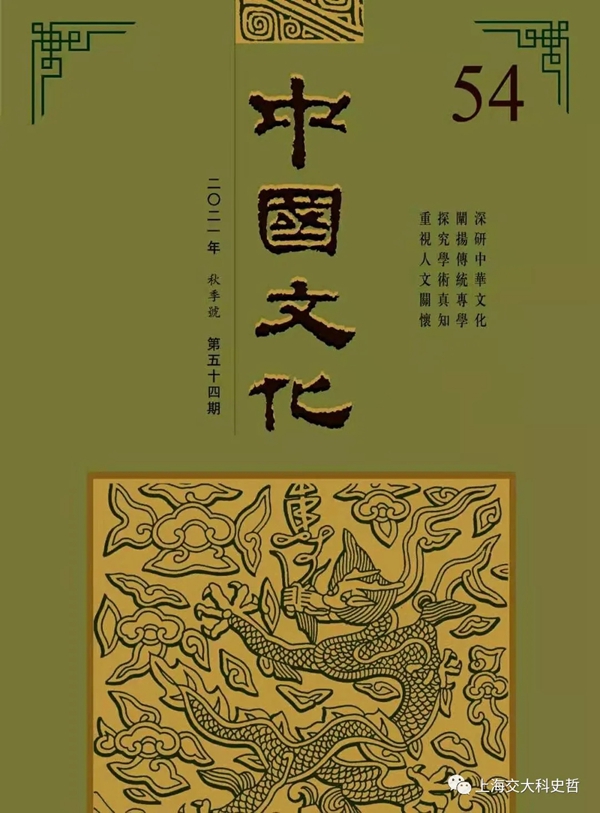
高禖之祀与仲春之会
——中国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
许多现代人习惯于将中国古代想象为礼法森然之礼教社会(尽管就整体而言中国古代任何时候也未出现过这种光景),而实际上,中国社会在上古时代充满了朴野、欢乐而又神秘的色彩。此种类似童年欢乐之光景,历数千年后,虽似已烟消云散,但昔日盛况及其流风余韵,依然可得而言。
一、高禖之祀
高禖之祀,后世逐渐湮灭无闻,然而此事实为中国上古社会生活之一大关节,自性文化角度言之,尤有重大意义。
《礼记·月令》言“仲春之月”诸事时云: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关于这段记载,杜佑《通典》卷五五有所解释,引卢植说谓:
玄鸟至而阴阳中,万物生,故于是以三牲请子于高禖之神。居明星之处故谓之高,因其求子故谓之禖,以为古代有媒氏之官,因以为神。郑但言后王,不知起于何代。
这里指出了举行高禖之祀的日期:春分日,即所谓“玄鸟至”之日。这一天太阳正处于黄道和天赤道的交点上,故昼夜等长,古人谓之“阴阳中”。玄鸟即燕子,作为候鸟,于春暖后北归,此为中原所见物候。燕子当然不会刚巧在春分日那天方“至”,举此日是着眼于其象征意义。由此亦可见古人阴阳天人感应观念之影响。
卢植又指出高禖之祀的目的是“请子”,即求子。《诗·大雅·生民》亦有“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之语,传曰:“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按“弗”即“祓”,“郊禖”即高禖,因祀高禖之所多在京城南郊,故云。
又《通典》卷五五解释称:“天子所御,谓今有娠者;礼:谓酌饮于高禖之庭,带以弓韣,求男之祥。”即带上经“雨露承恩”而已孕之妃嫔,前来参加仪式。这进一步阐明了高禖之祀与求子之关系。
关于高禖之祀的对象,卢植认为是“古代有媒氏之官,因以为神”。媒氏之官见《周礼·地官》(其职掌与高禖之祀有密切关系,说详下节),但如何转化为神,不得而知。另一种说法认为此神即女娲,罗泌《路史·后纪》二谓:“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也只是传说。高禖之神究竟为谁,另有殷始祖契之母简狄、伏羲、祖先、男性生殖器等说,各自都有一定的文献依据,最后一种理由相对比较充分。
而魏晋时代的高禖之祀,据《通典》卷五五所述,似乎并无具体神祗,而是“石主”,亦即某种象征物而已(比如阴茎的象征物)。又引晋博士束皙说,谓“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为主,祀以太牢也”,这明确显示,高禖之祀正是上古生殖崇拜传统之继响。
关于受祀对象虽异说纷纭,但在此处讨论中并不重要,自文化史角度视之,无论其为神祗或石主,其意义都是一种象征物。
高禖之祀中,除了上述《礼记·月令》所言仪式之外,还有舞蹈,称为“万舞”。
例如《诗·大雅·閟宫》中有“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之语,闻一多谓此处“閟宫”即鲁国高禖之祀的场所,并认为“是祀高禖用万舞,其舞富于诱惑性,则高禖之祀,颇涉邪淫,亦可想见矣”。[1]
又《诗·邶风·简兮》咏及万舞: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可见万舞为一种突出男性之力的舞蹈。朱熹《诗集传》卷二谓“万舞,舞之总名”,明显不确,太失水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的记载特别能说明问题: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
令尹子元是楚文王之弟,欲追求寡嫂,故振万舞以蛊惑之。注意文夫人在“舞”前面加了定冠词“是(这)”,表明子元跳的确实是一种特定的舞蹈。文夫人所云“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与《简兮》中所咏完全一致,与闻一多的判断也不矛盾——子元既思以万舞来“蛊”文夫人,则其舞之有诱惑性,可想而知。
令尹子元“振万”意在诱惑文夫人,还可以从《左传·昭公元年》记事中得到旁证: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子皙(公孙黑)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公孙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两家贵族争聘美女,经执政大臣子产裁决,让两贵族各自表现,由美女自己选择。公孙黑英俊多金,又盛自修饰,公孙楚却戎装表现自身勇武,左右开弓射箭,最后还展示了“超乘”(跃上奔驰中的兵车),于是赢得美女芳心。公孙楚这番表现,和令尹子元“振万”其实也就差不多了。总之在那个时代,男性的勇武,具有对女性的性诱惑功能,殆无疑义。而高禖之祀中的万舞,因有娱神唤春等功能,重在展示性诱惑色彩,尽管有可能真是来自“习戎备”的传统。[2]
高禖之祀的仪式,颇为后代所沿袭。据《通典》卷五五,举行高禖之祀的有两汉、魏、晋、北齐、隋、唐等朝:
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为高禖之祠于城南,祭以特牲。
后汉因之,祀于仲春之月。
北齐置高禖坛于南郊旁,广轮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岁玄鸟至之日,皇帝亲帅六宫,祀青帝于坛,以太皞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
隋亦以玄鸟至之日祀高禖于南郊,坛牲用一太牢。
大唐月令,亦以仲春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
晋代围绕对高禖之祀的认识,还有过一场小风波:
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高禖坛上石中破,博士议:礼无高禖置石之文,求知设造所由。既已毁破,可无改造。束皙议:以为石在坛上,盖主道也,礼:祭器弊则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废。
上古文献中确实迄今尚未发现关于高禖之祀置石主的记载。最早出现石主记载已是曹魏时代,《通典》卷五五:“魏禖坛有石”,“青龙中造”。故原先是否有石主,确是疑问。束皙的意见或有偷换概念之嫌:祭器与受祭对象为不同性质之物,石主当是受祭对象而非祭器。但如将“祭器”理解为祭祀中用到的各种器物,则石主作为高禖之神的象征物,谓之“祭器”也勉强可通。争议的结果是采纳了束皙的意见,依照原来式样造了一个,将破石埋入地下。
《通典》卷五五又云:“按江东(梁)太庙北门内道西有石,文如竹叶,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庙所得石。陆澄以为晋孝武帝时郊禖石,然则江左亦有此礼矣。或曰百姓祀其旁,或谓之落星也。”落星指陨石。联系到前述关于石主的争论,足见到南北朝时代,人们对于高禖之祀的情况已经不甚了了。
二、从高禖之祀到仲春之会
后世帝王所行高禖之祀,多半只是一个僵化仪式,但在上古,高禖之祀却是一派光怪陆离的撩人场面。
《墨子·明鬼》谈到燕王“驰祖”之举时插叙说:
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段话。乾嘉诸老对此异说纷纭,但因他们的思想不敢涉及“邪淫”,故始终不得要领。至闻一多、郭沫若,方始对此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闻一多谓此所言宋之桑林、楚之云梦,正是宋楚等国举行高禖之祀的地点(前引文)。郭沫若也持同样意见,他并进一步指出,“驰祖”之说与《诗·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及《周礼·春官》“凡国祈年于田祖”等记载,皆与高禖之祀有关:“祖、社同一物也。……古人本以牡器为神,或称之祖,或谓之社。祖而言驰,盖荷此牡神而趋也。”[3]
各国高禖之祀与仲春之会的关系,可以从古代文献中找到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娱神仪式和男女欢会,确为整个活动的不同部分。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对两者本身获得正确和深入的理解。
《周礼·地官》叙“媒氏”之官的职掌有云:
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奔者,“淫奔”也,即男女间的自由结合。此处不应将仲春之会理解成专为“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举行——“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是“媒氏”官员的职掌,未必仅限于仲春之月。此处的重点是仲春之会,即一种“奔者不禁”的性狂欢节日。
一些学者认为《周礼》之书,系平王东迁后某上层人士参考西周王室档案而作,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西周各种制度的面貌。在20世纪疑古浪潮退去之后,多数学者仍愿意相信《周礼》保留了许多上古时代的信息。
《周礼》记载的这种“奔者不禁”的男女狂欢聚会,已被现代文化人类学家确认为各民族非常普遍的现象:“仍然保留着的没有性禁忌的非规范性关系时期就变成了一些独特的节,这些节日的特征就是疯狂的、毫无约束的性交,即真正的放荡。……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这些放荡节日的多少遥远的遗迹的记载。”[4]
自周室东迁后,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即如高禖之祀,燕、齐、宋、楚等国都搞这类活动,故《诗经》中有许多篇什咏及此事,如《鄘风·桑中》《陈风·东门之枌》《郑风·溱洧》等,《诗小序》中也不止一次提到,比如“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野有蔓草),“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有狐)。所谓“失时”,指男女未能及时获得性爱。
桑中即桑林,那里既是祀高禖之所,又是男女狂欢之处,地点是一致的。而从时间上看,中(仲)春之月,即春季的第二个月,高禖之祀与仲春之会在同一个月,时间上也是一致的。再从情理和实际作用来说,两者也是一致的:高禖之祀本为生殖崇拜之盛典,在此吉日良辰,举行歌舞狂欢之会,青年男女谈情做爱,已婚妇女祈求多子,其宗旨与气氛都极为相宜。既然是“以弗无子”,则娱神仪式之后继之以实际行动,祈子得子,人神俱欢。
又仲春之会是由“媒氏”召集的,而据前述《通典》引卢植说,高禖之神系由媒氏转变而来,这也明确显示了两者的关系。
再进一步看,仲春之会这种男女放荡狂欢之会还有巫术色彩,被用来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前引《诗·小雅·甫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即为例证。男女狂欢可以用来求雨,这种巫术源远流长。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谓“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臧,女子欲和,而乐神”。又如梁武帝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以七事求雨,其六即为“会男女”。
关于燕之“驰祖”,已见前述,与此对应者为齐之社,先秦文献中亦有踪迹可寻。《春秋·昭公二十三年》云:“夏,公如齐观社”,对于鲁昭公此举,《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皆谓之“非礼”。为何观社即为非礼?《谷梁传》给了理由:“以是为尸女也”。
据《说文》:“尸,陈也,象卧之形”,郭沫若认为“尸女当即通淫之意”,那就是鲁昭公赴齐观社时享受了色情服务。而在先秦典籍中,“尸”也常用于姿势描述,比如《论语·乡党》“寝不尸”,如将“尸”理解为对女子的姿势描述,则“尸女”亦可理解为后世艳情诗歌中经常咏及的“玉体横陈”,那或许意味着鲁昭公赴齐观社时欣赏了色情艺术。无论哪种解释,都和闻一多“高禖之祀颇涉邪淫”的论断相符。
三、仲春之会的作用
关于仲春之会的作用,传统的说法是增值人口。此说虽总体言之不能算错,但也不无误解或误导之处。
仲春之会固有增殖人口的作用,但在先民眼中,这首先是因为举行了“以弗无子”的生殖崇拜仪式,邀神之佑,方得如此。而不是着眼于狂欢之会造成的具体受孕——那时先民是否已经正确认识到性交和怀孕之间的物理关系,目前也还缺乏明确证据。而且,仪式后的男女狂欢,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仪式的一部分。此种祈子祈年的巫术,在当时被视为国家大事,所以要求人人出席。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周礼》中“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的记载,方能圆通合理。
鄙意仲春之会更重要的作用,是为情欲之宣泄。不过这并不需要假定先民们平日被迫忍受禁欲的痛苦。盛大而热烈的男女狂欢之会,“奔者不禁”,无疑会给与会者带来与平日大不相同的欢乐,提供了与固定配偶(可以不止一个)之外的异性进行性爱交往的机会,这种机会在平日毕竟不会很多。
仲春之会上的情欲宣泄,也有生物学上的依据。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女性的发情期消失(也可以理解为扩展到了全年),但据一些西方现代学者的意见,此种情欲周期仍有遗迹,通常在春季,有时也会出现在秋季。比如霭理士(H. Ellis)认为:
世界上有许多分散得很远而很不相干的这种民族,在春季、秋季、或春秋两季,都有盛大的欢乐的节气,让青年男女有性交合与结婚的机会。在文明的国家,得胎成孕的频数也有它的时期性,一年中的曲线,大抵春季要高些,有时候秋季也比较的高,看来就是这种节气的一些痕迹了。[5]
其实关于情欲周期,中国先民早知其事,已将此事纳入阴阳天人感应框架中。比如《白虎通·嫁娶》云:
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诗》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二月,冠子、娶妇之时也。
关于秋季的情形,潘光旦注意到了《礼记·月令》“季秋之月”中的记载:“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潘光旦认为此处“务内”的“内”字,“不见得是注疏理所称‘收敛’的意思,而是同于《内则》的内字,即所务是‘男女居室’的事”。[6]
潘光旦的猜测是正确的,“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就是要求在季秋之月积极过性生活。此处的“内”就是性交之意,这样的用法之先秦两汉的典籍中相当多见。比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淳于意述病案,多次提到因性交而致之病,皆谓“病得之内”、“病得之饮酒且内”、“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又如《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此外在中国古代房中术著作中,也将阴茎插入这一动作称为“内”,如“内之”、“乃内玉茎”等等。
至于为何要“申严号令”,实与《周礼·地官》中“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同一原因。盖一者由于阴阳天人感应观念之影响,要求人人“循天之道”以行事,二者此种类似仲春之会的活动既有巫术性质,整齐划一应该是某种技术性要求。
四、简要结论
在生殖崇拜和阴阳天人感应思想作用下,春秋时宋、卫、燕、齐、楚等国都会于固定地点,在春分日举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神是谁,前贤尚无定论,后世高禖之祀中常以“石主”取代和象征之。高禖之祀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是万舞,这是一种起源与军事有关、因强调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诱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传统可能在西周已经形成,而在秦汉以后,仍被保持了很长时期。这个传统的目的是祈子,即祈求人口繁衍。
春秋时代的高禖之祀继万舞等仪式之后,是仲春之会,即一种可以放松性规范的男女狂欢之会。仲春之会由“媒氏”之官召集,活跃性生活同样有利于人口繁衍,同时也有助于青壮年男女释放情欲。这种男女狂欢之会也可以从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对其他文明中类似聚会的描述中得到印证。仲春之会同样有可能起源于西周甚至更早。这种男女狂欢之会还带有巫术色彩,被认为有助于年成丰收,故仲春之会后世虽不再出现举行的记载,但它的祈年功能被变形为祈雨等活动,这些活动中仍然强调男女之间活跃的性生活。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Offer Sacrifices to Gaomei and Spring CorroboreeExplo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ex Culture(1)Jiang Xiaoyuan
[1]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载《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第4期,后收入《闻一多全集》第1册,开明书店,1948。
[2]关于万舞与“习戎备”传统之关系,可参阅陈致:“万(萬)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与《诗》中三颂,收入《诗书礼乐中的传统:陈致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郭沫若:释祖妣,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
[4]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蔡俊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39页。
[5]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7,33页。
[6]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7,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