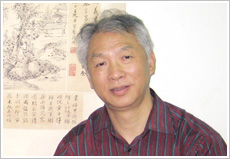张之先:伟大坚强的母亲
时间:2022-09-16 11:41:32 来源:故人旧事小编 作者:
伟大坚强的母亲
文/张之先
母亲和家
我的母亲叫邵侣志,原名邵菊仙。他生于1921年秋天,江苏无锡人,外公是一个地道的工人,在江苏无锡北门外张村邵巷,那是我们外公的老家。只要说邵大宝大家都知道。邵大宝是我外公。外婆这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妇女,她老人家泼辣性格影响了她的六个女儿。我母亲是老二,外婆连续生了五个女儿之后,才生了我舅舅,后来还想生一个儿子,结果第七个还是女儿,就再也没生了。七个孩子,六个女儿,一个儿子,那儿子就成了家中的宝贝。在家里面,我舅舅非常受到宠爱,几个姐姐妹妹都围着他转。

作者母亲像
在舅舅读大学期间,我们也很困难,但是我母亲每个月挤出五块钱来寄给他。那个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不到十块,一直到他天津大学毕业。舅舅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成了全家的骄傲。我舅舅比我大八岁,我读中学他读大学。舅舅每个月会从天津大学给我写一到两封信,鼓励我,教育我。在重庆广益中学读书的时候,收到最多的信就是我舅舅给我的。那些信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文化大革命,我去廊坊原子能研究所看他,他指给我看钱三强、何泽慧,那都是我们国家了不起的科学家,在当时都是被打倒的对象,他们跟平常的人一样,受到冲击。因为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这些科学家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培养出来的呢?
我母亲因为家里面都是女孩子,所以说要想读书是非常困难的,我母亲非常想读书,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人生,家里又养不活这么多孩子,于是就把她抱养给另外的亲戚。她告诉我,她小时候被那个亲戚卖给一个有钱人家的妾做贴身丫鬟。那个女人没有孩子,因此对她特别好,把她当做女儿,她也叫她姆妈。姆妈还让她去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她的文化也就是小学水平,都是那一个姆妈提供的。长大后在上海认识了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出身书香门第,又风度翩翩。她也想和有文化的人结婚,然后也去继续深造。抗战期间,父亲回到重庆考入内迁的复旦大学。我母亲也经过千辛万苦来到重庆,和我父亲结婚。可是结了婚之后生了孩子就只能当家庭妇女。哪个时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为了生活,只好随时跟着父亲到处寻找工作,走遍了很多地方。曾经最幸福的时刻是在北京和八公张大千老人家住在一起,在颐和园,那时候我才一岁多。
我母亲有一本相册非常宝贵,保留了在颐和园的当时许多照片,可惜文化大革命抄家之后就找不到了。到1946年我们家里是三兄妹,大姐,哥哥和我。1947年在贵阳的时候,那时我才不到一岁,我哥哥三岁,因为抗战胜利不久,日本人留下了一批药品,医生不知道那是毒药,以为是治疗儿童消化道的药。那天我的哥哥吃多了牛肉干不消化,就到贵阳著名的儿科医生陈聞达那里去看病,恰好服了这种毒药,几分钟就死了,当天一共有六、七个儿童不治身亡。 这时父亲在北京谋职,母亲带着我就和姐姐跟随父亲到了北京,住在颐和园。可以想象那一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我母亲也曾带着我和姐姐回到无锡乡下,有点衣锦还乡的感觉。在1948年又生了我妹妹绍佩,据我妈说,当时她不想要,但是祖父母要求生下来,于是就把妹妹生下来放在贵阳由我祖父母抚养。
因为父母两个人的原始家庭不一样,经历不一样,认识不一样,观念大不相同,而父亲家里面又是非常受宠。新婚没有多少久就开始吵架,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大女儿成了母亲的出气筒,我大姐从小就特别害怕母亲而亲近父亲。父亲在家里面得不到爱,曾经和家里的兄弟在外面去混。我母亲因此恨之入骨。一吵架就提到这事,并说你如果有八叔(张大千)的本事,你找几个我都不管!母亲发怒很让人害怕,有一次她将痰盂里面的屎尿泼在我五叔身上,她怪五叔把我父亲带坏了。从此以后我母亲在家里面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印象。 在张家,大家公认我母亲特别能干,能理家,打毛线衣打得好,但是对我父亲和子女的脾气特别不好,整个张家都觉得她太厉害了。我父亲特别害怕我的母亲,我姑妈开玩笑说,你父亲平常在兄弟姊妹面前做鹅颈状,非常高傲,因为他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但是看见你母亲来了,马上就萎了。
改变人生
1949年,国内战争已成定局,这个时候我父母商量,觉得国民党还是太腐败了,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肯定是先进的,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跟共产党走。他们都觉得自由了,可以参加革命,我母亲就去学习,在重庆茶叶专科学校读书。我父亲就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进军西藏。他文化高,当文化教员。父亲参军,母亲读书,我和姐姐,妹妹都在贵阳跟随祖父母生活。母亲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去做茶叶技术推广工作。当时贵州还很乱,她参加了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工作。他表现的非常的积极,跟当地的农民有很深厚的感情。我父亲是52年从部队转业到重庆一家工厂工作,因为他是学财经的,在工厂里当会计。
一直到53年,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到重庆父亲的身边,从贵阳到重庆要坐三天长途汽车,那个时候我才八岁。不久我祖父母也从贵阳来到了重庆。住在重庆市内,有一个地方叫南纪门,坎井街书帮公所3号,那段时间是我童年开始有美好回忆的时日。母亲是1957年才因照顾关系调到重庆肥料厂,是因为他是技术干部,虽然不对口,只能调他到化验室学做化验员。到了57年,我的九叔张心义被打成右派分子。 祖父母为了帮我的九叔,动员大家卖掉手上的国库券,也卖了书帮公所3号的那套房子,去了当时简阳洛带古镇。当时我祖父把重庆的房子卖掉,没有留给我们,于是我父亲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关系越来越恶化,父亲住进工厂,母亲带着我们也住在肥料厂一个12平方米的一个小屋里。我在市里就读树德小学(永兴巷小学)从二年级读到五年级转学到南岸四公里小学读六年级。1958年,我考上了凉风垭中学,在学校读住读。我大姐姐1959年在重庆20中毕业之后去到凉山昭觉,少数民族地区四川民族师范学校读书。 这个家从此以后就开始四分五裂了。 我和大姐最害怕看见爸爸妈妈吵架,我们看见他们吵架都觉得非常痛苦,又不能够从中劝说默默地忍受着这种痛苦。大姐读书离家远远的,她很难回到重庆。我也住校周末回四公里肥料厂。很难看到父亲母亲他们俩在一起,他们在一起总是不快乐。没有了家里温暖,大家就想躲避。父母关系不好,厂里工作不顺,母亲脾气越来越暴躁。我把被子从学校背回家,请母亲洗,母亲一边洗一边骂我大少爷,从此我再也没有把衣物、被子背回家给母亲洗过。有一次母亲骂了我,我就不回家了,很久没有回家,到了星期天我就跑到爸爸的厂里面去。有一天我和父亲到市里去,在解放碑附近,碰到了母亲和姨妈也在逛街,当时非常的尴尬。后来我看到了母亲的日记,她非常痛苦,说在大街上碰见我和爸爸在一起,她觉得心都碎了。这个失去温暖的家,给我幼年的心灵里带来极大的创伤。
刚直不阿的母亲
母亲可能天生就有一种渴望自由的感觉,家里女孩子多,她自己去上海谋生,抗战时期在上海遇到了我的父亲,于是他们相识相爱。我父亲回到重庆,在内迁的复旦大学就读,我母亲也来到重庆,他们结婚了。因为我八公张大千的关系,当时证婚人是于右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但毕竟由于张氏大家庭的歧视,母亲虽然能干,但一无所有。她觉得底人一等。她想读书,但是有了孩子,只能当家庭妇女。她和这个大家庭有许多不融洽。我父母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他们就发生了矛盾,常常争吵,当然,我父亲爱面子,总是我母亲占上风。虽然他们一辈子为了子女没有离婚,但是过得非常痛苦。
母亲是非常要强的人,年轻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江苏无锡,我大姨和她要去城里,人人谁有关卡要检查良民证。她们过关时 ,我母亲不给日本人行礼,我大姨给日本人一边行礼一边说太君,我妹妹是疯子,我妹妹是疯子!之后我母亲说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凭什么要给他行礼?大姨吓得不得了,说你不要命了!
母亲这个刚直不阿的个性,让她这一辈子过得很艰难。
一九四九年之前,为了生活,我父亲几乎一年一个地方找事做,母亲带着孩子跟着颠簸。我没有那段时间的记忆。从照片上看,我一岁左右和父母一起住在颐和园。母亲说,每天我姐姐牵着我走过雕龙画凤的长廊去打牛奶。我印象中父亲母亲分别抱着我在那个铜牛上的照片非常深刻。可惜文革整本相册给抄家了。母亲有时会讲起在颐和园那些画家于非厂,谢稚柳来看张大千,她去摘荷叶,煮荷叶稀饭给大家解暑。得到老人家的夸奖。
父亲由于得不到温暖,有一段时间也曾经外出寻欢,这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我母亲还反对打牌赌博,她说我辛辛苦苦存几个钱,输给别人了好心疼,我把别人的钱赢到自己的口袋其心何忍。在张家分两类,一类是打牌的,一类是不打牌的。我祖父母和八公张大千,我母亲是不打牌的,大千先生二夫人,我父亲和我阿妳(大婶)他们是打牌的。我从小就被我母亲教育,决不允许一嫖二赌。我们四个姊妹没得一个会打牌,不会打麻将,更不用说去赌钱了。并且我们都不离婚,都把家庭经营得还可以,都是因为受了父母亲的影响,他们吵架让我们不安宁,我们子女安家都不吵了,是不是很奇怪?四姊妹也没有哪一个在外面去乱谈情的。
正直的母亲
一九四九年后,人们没有迁徙的权利。父母才发现过去那种动荡的生活叫自由,是可以随心所欲选择自己满意的事业,不如意抬腿即走。如今一切都有政府的安排你,只能….不能…..。
在父亲多次申请之下,我的母亲终于从贵州调到重庆。结束了两地分居的问题。没有对口的单位,只能安排到重庆肥料厂,在化验室当化验员,跟她原来的茶叶专业一点儿都不同,她一切得从头学起。化验室的负责人姓罗,很斯文的一位阿姨。个头不大,带着一副眼镜,妈妈很尊重她。母亲是非常好学的,她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努力工作。
日子安好不到一年,大跃进来了。各行各业都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超英赶美。
厂里面就开始打擂比武了,各个车间都喊出口号,向党献忠心,深怕落后要被批判。这个班日产定额500斤,另外一班就提出要日产800斤,这一班不示弱,于是就喊出日产1000斤,那一个班更吓人?喊出日产2000斤!这怎能达到呢?于是就粗制滥造,将含磷极少的石头,打成粉,再加上磷酸混合,就是磷肥。
母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她在化验时发现这种肥料是不可以送到农村的,于是她强烈的反对这种浮夸风。我记得她曾经把造假肥料的事对我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是害人的啊!”
好大喜功的厂领导可不这样看,说我母亲右倾。于是就下放她到农场去劳动,改造思想,她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去了南川乐村农场。
下放一年回来就把她调动到车间去当工人。车间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粉尘相当大,劳动强度也大,这段时间母亲的脾气也大。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也开始撕裂。她找不到出气的,于是就会在我父亲和我们子女的身上发火。最倒霉的是我十一、二岁的大妹妹,因为逆反,又受到邻居的挑拨,我大妹妹还到会上去揭发母亲。 我母亲感觉到城市里太凶险,她觉得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刚好政府当时有一个号召:“不在城里吃闲饭”,动员城市的人下乡。于是母亲就决定不要这份工作,回老家江苏无锡当农民!外婆那边也同意了,母亲办完辞职,把户口寄了回去。
一切在筹备回老家就绪之际,母亲准备去贵州看一看她的那些老朋友,如果回江苏,去贵州就太远了。 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母亲从贵州回来,满脸兴奋,她改变了主意,她宣布不回江苏了,要去贵州当农民。原来她曾经工作的那个地方,安顺大西桥乡农民们已经把土地包产到户。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家家有余粮,与全国人民挨饿的日子大不一样。与她一起搞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那些同事,已经是公社的领导。他们特别欢迎她回去,答应给她分土地。我望着激动的母亲,不知道是祸是福。她是一家之主,没有谁能主宰她,没有谁能反对她。她从江苏把他的户口要回来,挪到了贵州安顺大西桥乡九溪村,带走了两个妹妹去当农民。她非常的自豪,以为她这一生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却不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无论她走到那里,都会因为她曾经和张氏家族的关系而被边缘化。 紧接着后面的一个个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几乎要了她的老命。
慈心善举的母亲
母亲落户到了九溪,看到当地的老百姓依然那么的迷信、落后。当地农村缺医少药,也没有卫生常识。最麻烦的就是生育孩子的风险太大,出生死亡率相当高。善良的母亲又决心帮助那些可怜的孕妇,她要当接生员,让那些母子平安。想到我的三姑妈张心素是妇科医生。于是就跑回重庆,向我姑妈请教怎么样接生。我姑妈说你胆子真大?母亲就把那些妇女的悲惨遭遇讲给我姑妈听,她的真诚打动了我姑妈,于是就教她怎么样接生?就这样,她拿着一本书,带着我姑妈给她教授的方法,回到九溪,就开始去为那些妇女接生了。

我当时还在重庆读书,每一年放暑假,我就会到贵州去看望她。这日子她过得非常的充实、开心,每过几天都有人来求她,有时三更半夜有人来敲门,急匆匆喊她:邵太太快一点,我家女人要生了!母亲一边答应,一边翻身起床,披上外衣,打着电筒就跟人家走了。一直到天亮,拖着疲倦的身体回来,但是她非常的开心,说生了个男孩或生了女孩,特别健康。然后她吃一点东西,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就睡了。
据说九溪村和附近的几个村里几乎六一年六五年出生的两三百人都是我母亲接生的。没有发生一起事故。
她的床脚是一些砖头垒起来的,上面铺一个门板, 在门板铺满了谷草,上面暖暖的,香香的。虽然不能跟我们过去的家相比,更不能和颐和园的条件相比。不管怎么样,母亲还是觉得她过得非常的快乐,她觉得她的选择很值。我陪她走在大街上,大街上的所有的人都热情地向她问候,老人叫她老邵,中年人叫她邵伯伯,邵姨妈,小孩叫邵太太。当地的村民叫儿子是大爷,他们都问:“老邵!这是你家大爷啊?”她也大大方方的把我介绍给当地的村民,她十分开心。我问我妈,我怎么成了大爷呢?母亲笑了说儿子就是大爷!我的两个妹妹就当了农民,他们十来岁就开始在那里务农,特别是我的大妹绍佩,十分能吃苦。母亲为了把两个女儿教育好,她费了很多心血。因为他会打毛线,所以说她也利用她的长处给当地的村民织毛衣,织头巾来增加收入。由于他改变了农村生育死亡率,当地的村民都非常地尊重他,他又讲道理明事理见识广,她在当地有非常高的威望。她也爱管闲事,村里一口公用饮水井,有村民不注意卫生,母亲就会去干涉,不许在井边洗衣洗菜。那些人看见我母亲在,都不敢乱来。
灾难深重的母亲
不幸的日子很快的就来临了,到了1965年,农村开展了四清工作,城里派来的工作组,把原来的一批领导撤换了,作为了解情况的人,母亲认为这些从土改过来的干部全心全意,毫无私心,凭什么把他们撤换了?有一天,风雨交加,社员们都去抢险去了,工作组在他们办公室拉琴唱歌。母亲忍无可忍,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朝着那些工作组的成员吼起来:“社员们都去抢险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拉琴唱歌?像什么话?”那些人都是从省里、市里派下来的干部,从来没有人批评过他们,他们就是钦差大臣,遭到这样一个女人的指责,他们非常的气愤,反问到你是谁?我母亲说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党的干部像你们这样!然后扭头就走了。有一个四清干部追到我家,追问我的母亲,你为什么不去抢险?我母亲告诉他,我的两个女儿都去了,正在这时,我的妹妹周身湿透了推门回来,那个干部见事不对,灰溜溜的走了,从此以后他们就知道在九溪有这样一个女人不好惹。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下子老账新账一起算。一查我母亲的老底,原来是张大千的侄媳妇!到农村来,肯定是逃避或者是干坏事,她那部收音机,一定是收发报机,那就是特务了。我的母亲当然不会服气,和他们据理力争,跟他们辩论。于是他们就把我母亲抓起来。安顺地区的房子,大多是坚硬的青石板做的墙,许多尖锐的棱角,他们抓住她的头发,在石墙上撞,撞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 母亲被五花大绑,押着她在五乡十八村游街示众,后来干脆就送进监狱关起来。在监狱里母亲不服,每天在监狱里高喊:“冤枉啊,冤枉啊!”闹得整个看守所不得安宁。看守所的所长只得给她说好话,说你好好的嘛,不要闹了,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没得权利放你啊!母亲在里面,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我和妹妹到城里面去给他申诉,许多有良知的领导对我们悄悄讲,再耐心等等吧。当时连国家主席都被打成反革命,你一个平头百姓挨了冤枉,也就冤枉了吧!全国这样的冤假错案,那真是无以数计啊!
苦尽甘来
最后苦日子熬过去,我父亲死不瞑目在黎明前,不幸中之万幸,我母亲终于见到了光明,给她平反了,她当了安顺县的政协委员。那个时候她可有些洋洋得意,她把她的政协委员的本子炫给我看,她给我讲她在监狱里的故事,讲她们九溪的风云,讲她被打、被斗、游街示众。吃那么多的苦,她还是喜欢九溪。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真的了不起!

落实政策可以安排一个妹妹顶替父亲,大妹妹已经结婚生子,只有小妹妹可以顶替。但是她不喜欢重庆这个地方,她说你把重庆送给我,我都不要。于是把指标转到贵州。她的工作安排在我母亲曾经指导过工作的安顺茶厂,当了一名工人,只有大妹妹绍佩还在当农民。我把母亲接到深圳养老,她和我的妻子相处很融洽,但是她已经不适应在深圳生活,我们都忙工作,她一个人很孤独的,只能在家里看电视。
于是她跟我说,我还是回九溪吧!我说我对你不好吗?她说好是好,但是你们都忙。我说你是不是怀念你的四类分子啊?她笑了!是的,她在九溪受很多人尊重,很多村民都会来看她,包括曾经一起受批判的那些“阶级敌人”。她走得动的时候,她也到各家去坐坐,大家都喜欢她。而她在我这里虽然衣食无忧,但是白天一个人在家,隔壁邻居是都谁不知道,新兴城市的冷漠让人倍感孤独。于是我只好同意让她回九溪。回到九溪,有大妹妹夫妇照顾她。
母亲在晚年有两次中风,但恢复都很好。我和母亲谈到生死,她很同意我的观点,生命在活着时去做喜欢的事,人死了什么纪念都没有意义,如果去世能捐赠眼角膜和遗体最好。但是贵州农村没有遗体接收条件,母亲说我死了就火化吧!不要树碑,把我的骨灰撒在九溪的自留地里。大妹妹在一旁反对说:那我每天锄地都要挖到你老人家的骨灰,我才不干呢!
在1997年的春天母亲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享年77岁。母亲年轻时最不喜欢的大妹妹给她送的终。我和妻子赶到九溪,几乎全村的大人都来家哭丧,可以感受到母亲在九溪的影响和威望。 母亲遗体火化后,我将母亲的骨灰紧紧地捧在怀里,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和依恋。我们驱车来到九溪村边的老青山下,我把妻子和两个妹妹留在山下,我由两个妹夫陪同,我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爬上山顶。我打开绸布,母亲的骨灰还是热的,好像那年母亲从监狱释放回来,我贴着母亲脸时的温度。 我的手捧起这温温的粉末,一边把她抛向天空,一边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呼喊;“妈妈!妈妈!妈妈!……. ”那凄惨的呼喊回声,随着风,带着母亲的骨灰在老青山的上空来回飘荡,久久不散!2022年8月于深圳

作者简介:张之先,自1993年涉及摄影,1995年以拍摄荷花题材到今已经二十余年,由于长期接触书画艺术界人士,拍摄艺术家肖像达两千余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重庆师范学院客座教授;深圳高等职业学院客座教授;2005年创建并被推选为深圳市老年摄影学会会长至今;
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荷花摄影展》。从1998年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武汉、成都、重庆、贵阳、昆明、顺德、澳门、泰国曼谷、澳大利亚悉尼、台湾佛光山等二十余地方和城市举办过展览和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