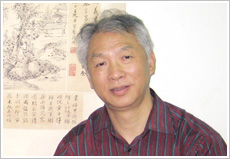陈佩秋:回忆潘天寿先生
时间:2023-08-11 15:01:54 来源:西湖l艺术 作者:陈佩秋
陈佩秋:回忆潘天寿先生

谢稚柳与陈佩秋
我虽从小喜欢画画,但对数理化的兴趣也很浓,成绩在班中一直领先。 所以,考大学前,有人劝我考艺术学校,说是画画今后能名利双收,而我却志不在此,考了西南联大的理工科,希冀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潘天寿
抗战期间,国立艺专等艺术院校多迁到了重庆,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一大批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等。 重庆靠近昆明,许多画家多至此举办画展,因此,那一段时间,昆明的艺术活动十分活跃。 徐悲鸿的画展,傅抱石的画展,李可染的画展……频繁的耳濡目染,重新引发了我对于艺术的天性。
1943年,黄君璧也到昆明来开画展。 黄氏以山水擅长,画法注重光影的渲染,云气水色,尤其逼真。 当时我对艺术境界的认识还不是很深,但从画画要画得逼真的角度,觉得黄君璧的画非常了不起,怎么画得这么好!在这个画展上,我拿出自己的一些习作给黄君璧看,请他批评指导,黄鼓励我报考艺术学校。 第二年,我即离开西南联大,跑到重庆,考上了国立艺专国画科。 当时艺专的校长是陈之佛,教授有黄君璧、黎雄才、张书旂、傅抱石等。
1944年,陈之佛辞去校长职务,由潘天寿先生继任。 这年秋天,潘天寿与谢海燕联袂到重庆,共同主持校务。 潘先生以校长而兼授中国花鸟画课程,并主讲古典文学、诗词及治印等,谢海燕任教务主任,授中国美术史论课,吴弗之任国画科主任,黄君璧上山水课。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令国立艺专回杭州,接受原国立杭州艺专校舍为永久校址。 直到1946年复原杭州完毕,于10月10日复课,陆续新聘教授有郑午昌、黄宾虹等。1947年,潘天寿先生辞去校长职务,由汪日章继任。 我从1944年考入国立艺专,至1950年毕业后到上海工作,足足有五年多时间的求学求艺生涯,其间种种人事变迁,指不胜屈,都已成了往事云烟,而潘天寿先生的形象,却始终是那样地清晰,那样地令人尊敬。

身为艺专的校长,潘天寿无论大小事务,多必躬亲,关心操劳。 他又是天生认真的性格,认真到近乎固执,这就更使他加倍地艰辛。 繁杂的学校事务,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除教务的安排外,甚至连学生的生活,他都亲自加以过问。 当时正当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重庆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常常断电,师生晚上的工作、学习,都是在菜油灯下进行的。 菜油由政府配给,再由学校统筹分给师生,数量相当有限,常常不够用。 当时的学生又很不礼貌,火气很大,经常与教师顶撞,甚至当面破口大骂,指责学校“揩油”,闹得很僵。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潘天寿总是亲自做学生的工作,苦口婆心地加以解释劝说,平息事态。 诸如此类的事,化去了潘天寿不少的精力,当校长实在是太累了,因此,1947年潘天寿辞去校长的职务,实在是有其苦衷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以图一个清静,专心搞他的艺术。

当时,潘天寿主要上花鸟班的课,一星期上一到两次。 我因在山水班,所以,正式听他的课不多。 但不久,听到大家都说潘先生上的课好,所以也偶尔到花鸟班去听他上课。 几次听下来,觉得潘先生的授课确实与一般教师不同。 一般教师上课,多要求学生学他的画风,临他的作品,如黄君璧教山水就是这样,凡是不学他的画风的,期末考试就打“0”分。 学生的反映很大,但不满归不满,也只能无可奈何。 潘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上课从不主张学生学他的画风,临他的作品,而是讲解基本的画理、画法,鼓励学生学传统,临古人的优秀作品。 他本人是画水墨大与意花鸟的,但不提倡学生学他,而要求学生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地作画。有一位来自乡下的学生,名字我记不得了,20多岁便留了一大把胡子,为人狂放得很,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叫“胡疯子”,他的画也如其人,胡涂乱抹,狂放不羁。

有一次他开了一个个人画观摩展,请潘先生去指导,提意见。 潘先生说他画得太野了,要收收心,规规矩矩地画,胡竟当面斥责潘先生:“你懂什么?”在场的人都很气愤,一个年纪轻轻的学生,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师长、校长,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潘先生却笑笑而已,由此足以看出其气度雅量。
当时的艺专学生中,不要传统,不要临摹,侈言“创新”的呼声很高,临摹传统,则被看作是没有出息的钻死胡同。 不仅学生这样看,有些教师也持这样的观点。而潘先生则坚持认为,学生学习阶段,必须在临摹传统方面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下功夫,不可耍小聪明,走捷径。 我们山水班上,以我临摹黄君璧最像,几乎可以乱真,有人便讽刺我是“黄君璧副牌”。 潘先生看了我的习作,却当面表扬我画得很不错。

对于传统,有的教师抱有很深的偏见,认为“南宗”好,“北宗”不好,文人好,工匠不好,意笔好,工笔不好。 如我看到五代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卷》珂罗版印本,对古人精工写实的本领钦佩得不得了,便化很大的功夫临摹了一本,拿去请黄宾虹指教。 黄看后不屑一顾地说:“这是工匠画,格调不高的,千万不要去临他。”我便请教怎样的画是好的?黄拿出一轴清代翁同龢画的水墨山石,其实是随意涂抹一通,像山石又不像山石,说这才是至高无上的文人画品。 我当时大惑不解,赵幹的画,千笔万笔,一笔不苟,无不殚精竭虑,,正所谓“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意匠惨淡经营中”,这样的境界,岂是一般画家所能轻易企及的?而翁同龢的水墨山石,乱笔涂抹而成,没有多少绘画技法的人也可以随便地画出来,怎么倒是至高无上的画品?还有对于工笔画,有些教师认为是“裹小脚”,今后无论怎样“放”,也是放不出“天足”来的。潘天寿却不是这样,他对传统不抱任何偏见,无论“南宗”还是“北宗”,文人还是工匠,意笔还是工笔,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凡是好的,即使是“北宗”,工匠、工笔,他也鼓励学生去学;凡是不好的,即使是“南宗”、文人、意笔,他也不提倡学生去学。 特别是学生阶段,他更主张从工匠的工笔画入手,即使今后选择文人写意作为发展的方向,也应以工笔为基础,否则便成了“野狐禅”。

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教学思路,1957年潘天寿出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1959年任院长之后,考虑到浙美花鸟画的教师多以写意擅长的实际情况,而我却从1950年以后专攻宋人工笔花鸟,因此,一度准备将我调到浙美任教。 后因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原因,我的调动没有成功,遂决定浙美的章培筠定期到上海来我处学习。从中国花鸟画史的发展来看,宋人的工笔虽然出于画院工匠之手,所达到的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并得到了当时的大文豪如苏轼等的认可,认为是“天机无穷出清新”的艺术描绘。 苏轼本人虽画水墨写意,但他对画院工匠的工笔画一点不抱偏见,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句,至今脍炙人口,这是他比后世的许多文人画家高明、宽容之处。 后来,文人水墨写意日趋发展,又有人片面理解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诗意为不要形似,不要生活,工笔画的发展遂日益凋零。

文人水墨写意当然也有高品,特别是这一画品注重画家主观情感的发抒,所达的成就,是工笔画所不及的,如陈淳、徐渭、八大山人等等,尤以八大山人的成就为最高,形象的高度提炼概括,笔墨的凝蓄蕴藉,还是从生活之中得来的;而徐渭却显得激情有余,观察生活不足,笔墨也过于狂肆,显得单薄了一点。 至扬州八怪及之后,所谓文人水墨写意,变成了完全没有生活依据的狂涂乱抹,其品格就不仅无法与八大山人相提并论,更不能以“文人画”去鄙视两宋院体工笔设色的工匠画了。

潘天寿对意笔、工笔的态度,不仅贯穿在他对教学的要求中,同时也贯穿在他目己的创作之中。 因此,他虽然可以称为是一位文人画豕,但无论他的艺术观点还是创作实践,都是与一般的所谓文人画家有别的。他早年走的也是一般文人画家的道路,学徐渭、吴昌硕,纵笔乱涂,气势有余,法度不足。 但不久即自觉地加以收敛,其苦心经营的严肃认真态度,比之工匠的工笔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曾与徐建融讨论中国画技法的发展,徐提到潘天寿的画法是“意笔工写”,这是很有见地的。
吴昌硕曾对潘天寿早年的画法提出批评,说是:“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慎尔独!”其实,这也是对一般文人写意画法的当头棒喝!写意画长于发抒画家的主观情感,而主观情感的无节制发抒,加速度越来越大,人的心态便不能平衡,画法亦越来越狂肆,两者如火上加油,,油上添火,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而以“慎独”缓“速”的“意笔工写”,则如悬崖勒马,不仅防止了写意画的直堕“深谷”,而且使写意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新境。

确实,像潘天寿这样的大写意花鸟画品,是传统中前无古人的,但它确确实实又是扎基于传统的基础之上,因此有传统大写意之长而又能避其之所短。遗憾的是,在中国画教学中,能体会潘先生这一苦心的并不是很多。
近代四大家中,我个人的看法,潘天寿、齐白石的成就在吴昌硕、黄宾虹之上。 但齐的诗文功夫不如潘,所以,其意境“俗”的因素多了一点,大俗虽然大雅,但比之潘天寿毕竟稍逊一筹。 同绘画创作一样,潘天寿的诗文也是认认真真地刻意经营而成的,法度非常森严。 在艺专学习时,国画科的诗词课由潘先生执教并上大课,所以,我算是他正式的学生,而不是如花鸟课那样只是旁听生。 课后我学做了几首诗词,拿给潘先生请他指点。 潘先生看了很高兴,说我的才气很好,但因古文读得少,所以不能畅达。 我认识到这一评语,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批评。 因为有“才气”的人往往凭小聪明不愿下苦功夫,而想方设法地走捷径。艺术之道与任何学问一样,都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就诗词与传统绘画的关系而论,从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苏轼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以及其他一些历代的大画家,无不以诗境为画境,以画境为诗境,庶几不堕俗品。 因此,从那以后,我便自觉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用以涵养自己的画品,虽然距潘先生的要求尚有相当的距离,但亦终身受益匪浅。 我毕业到上海工作后,潘先生还给我来信,说我“天资超逸”,又说“寓居沪上环境尤佳,书画定大有进步,有须至希一览成绩如何”。 如此等等,更使我加倍警惕,要以“天资”与苦功相辅相成,并充分利用上海的有利环境,使自己在艺术上不断取得真正“大有进步”的成绩。
以上所回忆的,是我在艺专求学期间及到上海工作后对潘天寿先生的点滴印象,虽然只是一些平凡的琐事,但也可窥见中国美术教育界和中国画坛一代师表的风范。